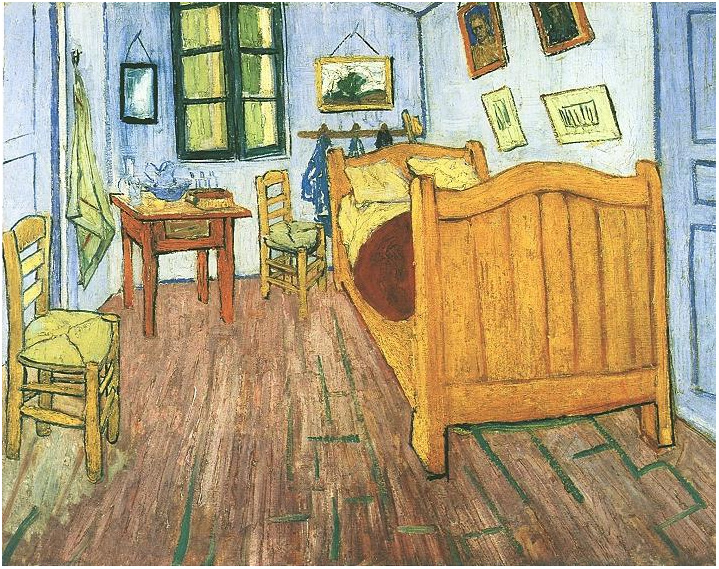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夜幕低垂時分經過童年居住過的大廈,只見頂層寥寥無幾的窗口有着零星燈光,其餘都烏黑一片,十室都已九空,估計沒多久,這些寥落的燈火也會一一熄滅,大廈也就被迫功成身退,隱入兒時記憶了。樓底下的商店老早都已全關了門,往時燈火通明的騎樓底,絡繹往復,頗聚人氣,但現在卻成了老外所說的ghost town,有點人跡罕至暗淡無光。旁邊兩棟相鄰舊洋樓也已被人收購待拆,樓下貼滿地產公司在香港別區成功收購的舊樓房照片,不日重建,好不炫耀。
大廈樓高十二層,以梯角型盤踞在電氣道及歌頓道上,像一座厚實的城堡,卻又光明磊落的在外牆上開着密密的窗口,一點都不欺人。大廈沒名,只叫街道號,不知何時落成,估計至少已在此地段屹立五六十年光景,見盡變遷。過去正對面是警察局、警察宿舍及籃球場,時移勢易,現已變了商業高樓及多層街市了;過去街道是雙向行車,路中間的欄杆在陽光普照的日子裡總掛着綿綿不斷五顏六色的床單棉被,但現在馬路只單向往東走,許是社會富裕了,再也沒人需要晾曬棉被了,街道上也就失卻舊時樸實的庶民色彩。
相信過去的業主都是老實人,大廈的建築似全用盡所佔的地盤,大廈的外牆邊即是騎樓底行人路的邊沿,一點空間都不浪費,什麽發水全無聽聞,一分錢真的一分貨,樓層裡的房間寬敞十足。樓宇設計採用懸臂樑結構,底下即成有蓋騎樓,是真正的公共空間,是街道的一部份,無論烈日當空或滂沱大雨,行人經過有蓋遮頭,都可駐足暫歇,不會被人惡聲驅趕。騎樓底也是小孩子的遊樂場,有時在此嬉戲追逐,玩得太過份也是會給大人叫停,但如果靜態點的跳飛機、擲汽水蓋、打波子,這些遊戲好像也不大打擾人,大人也就任得小孩們盡興開懷了。
時光飛逝,騎樓底下的商店換了又換,但印象最深的可能還是兒時的那幾家老店,有照相館,有中藥鋪,有士多辦館。照相館名風度,在小孩子的心目中是一家高級的店子,如不是什麽重要大事如上學、辦証件、跟回港探望的親人合照,難得進去光顧;向街的櫥窗掛着館主的黑白彩色作品,都是些人像照,有一家大小雙親坐前三五子女站後,有妙齡少女眉目含笑,也有小學生穿著校服正襟危坐;而每當自己進去拍照時,總是緊張兮兮似笑非笑地望着那蓋着黑布的龐大攝影機,每回拿到照片看着相中自己卻總有別扭的感覺,總不滿意。照相館旁邊是中藥鋪,掌櫃好像總是個老叟,他背後的百藥櫃一個個小抽屜由左到右由上到下排滿整道牆壁,有時小孩子有一兩毫零用錢也會去藥店買東西吃,嘉應子山楂餅得力素糖等是也。要買零食更多的是去拐角的辦館士多,買汽水買雪條,炎夏季節小孩將手插進汽水櫃的冰水裡也是一種透心涼的享受;士多另一邊是辦館,柴米油盬醬醋茶,好像也經常替媽媽來買這買那,辦館內一個個雪白小山丘,每個山丘都插有長長的木片,木片上寫着什麽米多少元一斤,標示價錢的那套數目字,現在都沒人寫了,就算還沒失傳,現代人可能都看不懂了。
八十年代初樓下開了一家茶餐廳,名叫珍寶,茶餐廳前身好像是家理髮店,印象已很模糊了,但珍寶茶餐廳卻有十七八歲的一些生活印記,好多個晚上都會跟住樓上的同齡好友到此喝杯東西聊天,記得曾說這會是自家的黃金十年,錯過了它,人生將會是個早來的句號。珍寶茶餐廳前不久才結束營業,許是租約期滿吧,它在這裡度過三個十年,人生多少個十年,不知有沒有黃金,捨或不捨,幾許風雨後,終究也要劃上那最終的句號了。
八十年代初歌頓道上也開了一家叫經典的照相館,專門拍婚紗照,店主是一位知名的攝影家,他創業、娶電視明星、生兒育女、移民他鄉、回歸香港,但或在漫漫人生路上與佛有緣,最終毅然抛棄塵世一切,包括妻女,在台灣佛寺剃度出家,法號常霖。婚紗照相館已關門很久了,店主也已開展自己的另一生命,而這如鬼域的騎樓底,那些老店老鋪會否也在另一國度輪迴重生?自家的黃金十年錯過了還會再來嗎?